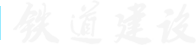“书记,今早食堂做了红薯粥,您最爱吃,大厨给您留了一大碗呢!”
“谢谢,大家有心啦!”
周六清晨,步入项目部食堂,果然桌子上放着一碗香喷喷的红薯粥。
我出生在乡村,对红薯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地区比较贫困,红薯是作为主粮存在的。不仅如此,红薯梗、红薯叶,也使家乡无数人得以果腹,给清贫的日子带去丝丝甜蜜。
农人把它当宝,每年六月份,早早地将红薯栽进泥土中。秋来,赶到霜降前,再把长成的红薯刨出来,一部分用来漏粉条,一部分当作口粮,剩下的则放入红薯窖储存起来。这样,可以吃到来年春天。
母亲最喜欢让我到窖中取红薯,因为窖深,且空间狭窄,孩童个小,手脚也灵活,下窖相对便捷些。她拿来一根结实的大绳,从我的脊梁骨后面绕到我的胸前,打一个结,再绑上一个竹篮,确定绑紧不会松动后,再麻利地掀开红薯窖上那个厚厚沉沉的大圆盘,用绳将我提溜着,从窖口一点一点慢慢地放到窖底。窖中浓浓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刚往竹篮中放了几个红薯,我的棉袄、棉裤上便沾满泥土。盛满后,向头顶上方喊一声:“妈,红薯装好了,快拉我上去!”
彼时,窖外,能够清晰地听到母亲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搓搓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我拉到地面上。
接着,母亲从竹篮中挑出几个红薯,洗净后削皮切块,倒入锅中,再添置一些水,盖上锅盖,点燃灶膛中的柴火,慢慢烧。
待红薯粥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母亲掀开锅盖,用勺子试试粥的黏稠度,太稀没味道,太稠又喝不了,很是讲究。母亲在长久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经她手煮出来的粥总是刚刚好,老人小孩都挑剔不了。盛出几碗粥端到饭桌上,又从菜橱中拿出腌制好的萝卜干、咸鸭蛋,招呼家人赶紧坐下来吃晚饭。
少时的冬日黄昏,窗外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们一家人整齐地围坐在屋内桌子前,喝着甜糯的红薯粥,吃着寻常小菜,说着笑着,其乐融融。
后来,通过考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四海为家的筑路人。多年来,脚步行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外面的世界虽丰富多彩,但我却无时无刻不再惦念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情系着故土的父老乡亲。
那一份亲情,早已在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红薯粥中化作最柔软的光,照亮我此后人生的漫长岁月。
朱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