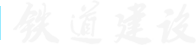香菜泡在水里,渐渐舒展,它特有的清香愈来愈浓,扑鼻而来。人行通道里摆菜摊,满脸褶皱的老人家递过来一把香菜:“这个特别香,煮面都好吃。”
果然,午间的面,格外香。
记忆里,第一次见到香菜是在工程队工人开发的一片菜地里。暑假,赶上半个月才休班一天的一个周日,母亲带我沿着新建大沙铁路的工地从新塘乡步行去瑞昌县买新衣服,二十几里地,又晒又渴,乏累盖过了穿新衣的期待,我越走越慢。“看到了没有,趟过前面那条河,我们就到瑞昌县域了,离城里也就不远了。要快点走,下午还要赶回来呢。”母亲催促。
一个整编制的工程队在河畔驻扎,正值下班,拿着工具的工人们乐乐呵呵地往回走。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翠娥,邓翠娥。” 牵着我靠边走的母亲抬起了头,是她同乡,一同招工入路的王叔叔,“这是茂妹子吧?都长这么高了。”王叔叔清瘦精干,他跑了过来,得知我们要去瑞昌,热情地邀请:“那还有段路,难得碰上了,就先到我那里吃过中饭再走。”母亲以赶路为由拒绝了,但架不住王叔叔的执着,我们跟着到了工程队。王叔叔住在大工班,特地跟指导员打了招呼,借调度室招呼老乡用餐。他从食堂打来饭菜,居然有一份红烧肉。母亲看了看,欲言又止,等王叔叔坐定了,她突然说:“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块芫荽地,好久没吃了,真是馋得慌。”“好,那你等等,我去扯一把。工班里几个河南人种的,他们管它叫香菜。”我记得,母亲那天中午只吃了香菜。她在王叔叔去拔香菜的空档,再三叮嘱我:“一会红烧肉不要吃,这至少是你王叔叔一个礼拜的伙食标准。我们留着给他打牙祭。”王叔叔不停地往我碗里夹红烧肉,我吞着口水,直躲闪:“我不吃肉,不吃肉。”母亲也帮腔,“是呢,打小她就吃荤菜少,随她。”于是,我第一次品尝了香菜,那不可言说的辛香味道让我若干年都不曾再品它一二。
香菜的根,我保留了下来。它让我想起了姨。姨特别爱吃香菜根,用辣椒豆豉爆炒,满屋香喷喷。大炼钢铁时期,外婆家的铁锅都被丢到炼铁炉里去了,外公外婆也被喊去烧火看炉子。镇上的大食堂午间十二点准时敲钟,四五岁的姨脖子长挂着一副碗筷,就会一个人跑去大食堂,看着天天清一色的熬萝卜,自言自语:“宝宝爱吃青萝卜,宝宝爱吃青萝卜。”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人们对集体主义近似狂热的崇拜,让一切变得有序又无序。外婆交代她的小女儿我的姨自己在家玩耍,听到敲钟就去大食堂,“只有熬萝卜,宝宝要是不吃,就会饿肚子。你就告诉自己爱吃青萝卜,姐姐听到了就会给宝宝从学校带好吃的回来。”外婆的大女儿我的母亲当时是镇上考上初中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在镇中读书的母亲每个星期六会把学校食堂做的偶见油星的水煮白菜之类的一份菜带回来给姨补充营养,这其中就有爆炒香菜根。
参加工作后,走南闯北,香菜几乎是每个餐桌上的座上宾,而我多是不向它伸出一筷。一次,吃烧烤,同事端上来一盘烤好刷了辣椒油的豆皮包香菜,坚持让我尝尝。出于礼貌,我拿了一根,孰料,竟然美味。“呵呵,下次你再试试香菜涮火锅,那味道更妙。”同事笑。自此,香菜渐渐被我接受。
李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