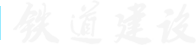说起劳动,我总会想起鲁迅笔下的“杭育杭育派”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在遥远的盘古开天的时代,九条黄龙在息壤间翻腾,赤足丈量山川的先民们,肩扛木石的号子应和着惊涛。正如《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如燧石相击,迸发出狩猎时代最原始的诗意。粗糙的竹弓在月光下绷紧,飞旋的土弹穿越万年时空,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震颤。
千年后苏轼的《密州出猎》里,锦帽貂裘的太守在平冈上纵马,箭镞破空时溅起的却是权力与诗意的双重涟漪。当劳动从生存必需蜕变为精神仪式,那些沾着泥土的“杭育”声便化作平仄相间的词牌,在青史长卷中生长出新的枝蔓。就像敦煌壁画上飞天的飘带,本是匠人修补洞窟时扬起的灰泥,却在时光晕染中幻化成漫天流云。
这种文明的嬗变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愈发清晰。孙少安在砖窑升起的青烟中寻找尊严,孙少平在矿井深处触摸星光,黄土地上每个躬身劳作的身影,都在用汗珠书写着存在主义的诗篇。当双水村的晨雾里响起第一声锄头叩击冻土的声音,整个黄土高原都成了摊开的稿纸,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藏着比十四行诗更深刻的韵脚。
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飞鸟纹饰,到当代治沙人在腾格里沙漠种下的梭梭林;从都江堰汩汩流淌的千秋智慧,到现代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培育的耐盐碱水稻,那些改造世界的力量,始终带着粗犷、有力的劳动号子声。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里,挑水僧人踏过的石阶与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上标注着相同的刻度。所谓奇迹,不过是劳动的双手,于平凡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默默耕耘,才让荒芜变沃野、让梦想成现实。
我是一名筑路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待筑的土地。在施工现场,我与工友并肩,把控工程每一处细节;寒夜里,我们共商方案,攻克技术道道难关。以信念为基,用担当作梁,用劳动搭建通途,让条条坦途跨越山海,见证我们为时代铸就的荣光。
回溯往昔,劳动的诗篇从未断绝。我恰似八千年前河姆渡的稻种,在岁月长河中历经传承,至今仍在江南的春风里翻涌成浪。或许每个时代都需要重新发现,真正的诗行从不在那宣纸之上,而是深藏在老农掌心的沟壑里,闪烁在焊枪迸溅的星火中,更谱写在所有把劳动号子声化作生命乐章的手掌之上。 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