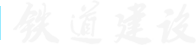6月上旬,在网上商城下单一箱五香花生米。打开密封袋,将花生米放入口中,牙齿轻咬的瞬间,先是感受到外皮微微的韧性,接着“咔嚓”一声,花生仁在齿间碎裂开来。一股浓郁醇厚的香气瞬间在口腔中炸开,那是八角、桂皮、香叶等多种香料交织融合的味道,与我记忆中的味道极为相似。
在我的老家,家家户户都种植花生。春天,先把花生米埋进土里,待到九、十月,便由农人一株株拔起,抖落泥土,排在地垄上曝晒。那花生荚壳黄白相间,裹着泥土的腥气,却也透出一股子清香。
彼时家境贫寒,花生虽不是昂贵之物,但也不得随意取食。母亲将晒干的花生装入麻袋,大半要挑到集市上卖钱,换些油盐酱醋回来。剩下的,便藏入瓦瓮,封了瓮口,置于梁上。我每每仰头望那瓦瓮,只觉它高不可攀,里面的花生仁想必是极香甜的。
学费是必须交的。父亲常常蹲在门槛上,用粗糙的手指捻着几枚祖上留下来的古铜钱,数了又数,末了叹口气,从瓮里舀出一升花生,次日便换回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来。
父母自己是不吃的。偶尔有客人来,母亲才从瓮中抓出一把,在锅里略炒,端出来待客。那香气便从门缝里钻进来,勾得我腹中馋虫乱爬。我扒着门框偷看,只见客人将花生仁嚼得咯吱作响,嘴角溢出些许碎末,竟使我生出几分嫉妒来。
实在馋得紧了,便去收过的花生地里“拾秋”。秋收过后,田里总会遗落些花生。我在枯黄的藤蔓间翻找,有时竟能拾得半篮。回家路上,心便跳得厉害,仿佛做了贼一般。
母亲见了,也不责备,只将花生洗净,放入锅中,加盐水与五香粉同煮。煮熟后捞出,置于竹筛上晾干。那花生米吸饱了香料,外壳微微皱起,显出几分饱经沧桑的模样。
父亲晚间劳作归来,母亲便盛出一小碟五香花生米,又温了半壶烧酒。父亲盘腿坐在炕沿,捏一粒花生,在指尖搓去红皮,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再啜一口酒,眼睛便眯成一条缝。我蹲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有时会分我一粒,我便学着他的样子,先搓去皮,再放入口中,用牙齿轻轻咬开,那香气便在口中炸开,咸香中带着丝丝甜味。
有一年大旱,花生歉收。瓮中的存货早早卖尽,地里也拾不到几颗。父亲喝酒时没了下酒菜,只是默默地啜饮。我见了,便去邻家收过的地里再寻,竟意外掘到一小窝遗漏的花生。欢喜地捧回家,母亲照例煮了五香的。那晚父亲多喝了一盅,摸着我的头说了句“好小子”,便沉沉睡去。
如今市场上的花生,各种口味应有尽有。我在超市、小店多次买过五香花生米,不过鲜少能嚼出当年的滋味,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泥土气,或许是父亲指尖的温度,又或许是那种在贫瘠中寻得一点甜头的欢喜罢。
花生终究只是花生。
变了的是年月,是人心。可不变的是记忆深处那缕醇香,是父母为生活奔波却仍尽力护我周全的爱意。那五香花生米的滋味,早已融入血脉,成了我心灵的慰藉。每当尝起,过往种种便涌上心头,提醒着我莫忘来路,要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在岁月长河中坚定前行。 詹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