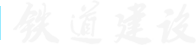王依卓
我时常忆起那片金黄,一列列、齐整整地立在外婆的旧院前。那是外婆亲手栽种的向日葵。她照料花草、果蔬、庄稼的样子,像是在泥土上写诗,锄头起落间,新绿冒出,日光沐浴下,灿黄绽放。
记忆中的花儿,从未凋零。
篱笆边攀着丝瓜与黄瓜的藤,圆叶在风中轻摇,黄色小花藏于其间,如星子般明亮地眨眼。南瓜则喜伏地而生,长蔓逶迤,一路延伸,仿佛有心事要诉说,有远方要奔赴。那远方藏着什么?外婆笑着说,是光照来的地方。我想,南瓜一定是大地的诗人,把每一句心事都吟成花,朵朵明艳,字句鎏金。还有一种外婆唤作“乌子”的植物,它沿墙爬升,郁郁葱葱,最终把整面土墙包裹成绿的帷幔。盛夏某天,花突然全开了,整堵墙变作金色的瀑布,叫人移不开眼。
可最让我念想的,仍是葵花。
它们站得笔直,神气昂然,终日迎着日光抬头。小时候我不服气,总想用手把它硕大的花盘扭过来,叫它看我、不看太阳。可刚一松手,它便毫不犹豫地回转,依然朝向光明,那般固执,又那般庄严。
后来我知道西方有个画家,为葵花作画,说它们像火焰,是“爱的最高光芒”。我的外婆自然不知梵高,也不懂什么艺术隐喻,但她知道什么时候下种、何时收割。在清贫却明亮的岁月里,这一院葵花,为我们镀上了一层暖色。花开之后,就有瓜子可吃——那样的期盼,是童年最踏实的美好。
待花盘成熟,它便渐渐低头,仿佛谦逊的智者。籽粒日渐饱满,日夜吸收阳光、承接风露,终成一盘密匝匝的蜂窝。外婆小心地割下它们,在匾中轻轻拍打,瓜子便如雨点般落下。晒着的瓜子,都还带着太阳的香。外婆说,每颗瓜子,都是葵花舍不得散去的魂魄。
她用慢火炒熟,然后一一分给我们,塞满每个孩子的衣兜。直到今天,葵花子的香气仍未曾散去。
如今外婆虽已年迈,但那葵花依旧年年盛开。它们不语,却仿佛一直在讲述着她的故事:一个女子,如何以土地为绣布、以光阴为针线,把最深沉的爱,都绣成了花。